逝者如斯,
写者如役。
——娜姐
汽车的喇叭声从马路上传来,偶有偶无。
穿堂的夏风摇动窗外满墙翠绿的爬墙虎,就像吹动一墙无法言说的心事。
无处停留的两只麻雀,在院墙上跳过来又跳过去。
天空阴霾,雨水未来。
我打开电脑,第一次如实如是书写自己上班14年的点滴过往。
逝者如斯,写者如役,如若停笔,生命何去。
一切需要从头说起。

真相有多近
2003年7月,大学毕业的第二天,我成为一名地市报的新闻工作者,与一帮男同事一道在报社热线部开始夜班白班连轴转的职业生涯。
方便面就着白开水的日子里,我曾多次第一件赶赴车祸现场与命案现场,也曾在凌晨三点起床曝光私自兜售白条猪肉的违法商贩,还曾在深夜零点随公安人员查办黄赌毒,在茶馆里无意撞见一对正在嘿咻的男女……
至今,我仍记得,坐班车、坐摩托、坐三轮去乡村僻壤,追问从教学楼上纵身一跳的少年,缘何以如此极端的方式结束自己的如花生命的往事。
也记得在一路灰尘飞扬一路机器轰鸣中,我坐着投诉人的手扶拖拉机上,到某县某镇某村调查假种子坑人事件之始末。
还记得曾孤身来到革命老区,秘密约见一位又一位受害人后,独家报道出某地公安民警受贿徇私枉法之真相……
斗志昂扬,激情饱满,愤世嫉俗,求急求快,是那时工作之特性,也是彼时我心之特点。
从2003年到20008年的5年间,我像一位手握利剑、赶尽杀绝的英雄,在追问事实真相和书写监督报道的道路上无法停下。
所幸的是,那时的网络没有今天这般发达,舆论监督的生存空间却比现在要阔大许多。
当然,我也收获了信任与认可。
我因关注民生,喜说真话,被百姓和读者追到报社感谢。因绝收红包,不徇私情,被领导和同事纷纷点赞。因文采飞扬,作品优秀,获得全国晚报最高奖。
只是,停下来的漫漫长夜里,我感到迷茫又孤独。
迷茫 ,是我常问自己:这就是我青春的梦想么?这就是我书写的真相么?这就是我为这座城市这片土地所能做的事么?
我的回答,并没有文章写得那么铿锵有力。
所谓孤独,是我翻阅过往的报道时,发现里面有眼泪在默默流淌,有伤口有在汩汩流血。
我曝光的贩卖假种子的经销商其实是位家中有幼儿患病有老母卧床的下岗工人,他也是位不明真相的受害者。
因我的一篇报道被撤职的民警,不过是整个丑闻里最容易被吃掉的那枚棋子,而我所谴责的那位当上经理的杀人犯不过是钻了一帮不作为公职人员的空子……
我开始对自己书写产生了深深的怀疑。
用批评的方式爱一座城市固然没有错,但如果所谓的书写不过是谎言的另一种掩饰,书写的意义又何在呢?
聊胜于无。我曾这样安慰自己。
或许,所有的书写都是极其有限的表达,不管是文学还是新闻。

暴戾有多恐
5年的舆论监督采写中,我也逐渐认识到,或者,比谴责更有力的是宽容,比憎恨更有力的是接纳,比暴戾更有力的是温和。
很多人很多事之所以无法善始善终,在于愚昧与劣根,在于冷漠与疏离,更在于对法律的无知和信仰的缺失。
如果,能以自己的有限之力,在推动他人意识的荒原上前进一毫米,那一定是件有意义的事。
那时,年轻如我者,依旧想着改变他人改变周遭。
直到多年后,我颈椎疼痛一身病患地步入中年,才明白:这不过是一厢情愿。
谁都无法说服谁。所谓和解,不过是我们都需要自己说服自己的那段时光。
谁也无法改变谁。所谓影响,不过是我们向好的心从他人身上看到的光亮。
谁也无法治愈谁。所谓治愈,不过是在漫长的交战与休整中我们终于搞定了自己。
但我依旧想为不死的新闻梦,做点什么。
2009年开始,我开始到政法新闻部。
两年多的时光里,我书写表面的罪与罚、伤与逝、亲与疏、爱与恨,也追问深层的因与果、强与弱、利与益、善与恶。
2009年至2011年,正是警民关系颇为紧张的两年。
我亲眼看到上访无门、走投无路、生无所依的人,如何把心里的怒火和哀伤一股脑儿地倾泻到出警的一线民警身上,我也亲眼目睹了疲于奔命、苦于检查、忙于破案的民警,如何把职业的焦虑与疲惫一下子地发泄到不愿伏法的嫌犯身上。
虽然,我没能把这些见证写到我的新闻作品里,但疲惫不堪的夜梦里,它们依旧化成张牙舞爪的怪兽与面目难辨的鬼魅,一步步向我逼近。
对立与较量、压力与暴戾、愤恨与发泄,成了这个时代很多人内心深处潜伏的幽灵。只要寻得出口、时机恰当,它们就会从困住其身的小魔瓶里钻出来,化成庞然大物,变成吃人魔兽。
你,我,他们,我们,概莫能外。
我深感恐惧,又略感庆幸。
恐惧的原因,是生于80后的我,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自我出生起,市场为王、利益为天的交易就开始崛起繁盛。
而所谓的道德伦理、价值文明、节操信仰,都在一步步沦陷,一点点瓦解。
庆幸的原因,是记者这一身份,让我有幸见证这个时代裂变之下的焦灼与国殇,也让我比同龄人多些怜悯与仁慈:一切并非如你所见,一切并非如你所说,一切并非你所恨,一切也并非你所爱。
在不停的书写中,我想:或许,这个信息爆炸、谣言四起、成功至上的年代,并不需要太多优秀的人,但迫切需要各式各样能够带来和平的人,能够疗伤的人,能够修复的人,能够讲故事的人,真正有爱的人。
我知道自己卑微又渺小,但我想成为这样的人。

梦想有多远
在我生活的这座三线(或四线)小城里,像我这样常年书写籍籍无名的记者有很多。
我不孤单,也不委屈。
2011年开始,根据单位工作的调整和个人写作的特性,我开始为那些挣扎在底层卑微又高尚的小人物书写。
我写他们的泪笑歌哭,放弃坚守,困顿迷茫,也写他们的质朴真诚,达观向上,不屈不挠。
在城市的老街老巷,在乡下的田里地里,在山中的云间雾间,在河畔的石旁水旁,那些身穿布衣布鞋,生有缺陷缺点,心有素魂素心的人,仿佛我的父老,我的姊妹,我自己。
我书写他们的故事与情感,就像把自己一点点打开,再一点点合上。
6年的时光里,我写了千余名小人物的故事和情感。他们每个人都如微尘般存在,又都像弥山般独特。
他们中有干着最累的活儿拿着最少的钱却收养一群孤儿的环卫工,有家徒四壁身无长物却把存款捐给贫困孩子的光棍汉,有身负重伤默默隐居从不向怜悯说不的老兵,还有面对不公和戕害依旧坚持寻梦的青年……
是他们,让我看到了这个繁华而急躁的年代里那些苦难而缓慢的人生;也是他们,让我触摸到这个变幻而功利的世界里那些质朴又璀璨的心灵。
或许,这个时代的灵魂恰蕴含在这些卑微而高贵的人身上。我想。
资本控制一切的当下,没有人脉没有金钱没有地位没有尊严的他们,怀揣怎样赤诚与信仰,才在大难临头与大敌压境时,依然挺起不屈的脊梁筑起这个国家最阔大的民心资源?
我还没有想明白这个问题,就遇到了现实的当头一棒。
经济一片萧条,纸媒生存堪忧。伴随一家又一家报纸的关停,一波又一波的余震在我脚下晃动。
一拨又一拨当年叱咤风云帮别人维权的无冕之王,不得不集结成对、摇旗呐喊,为自己的生存与饭碗投诉申辩。
街头的报刊亭在逐渐消逝,很多报纸不曾被翻阅就扔进了垃圾桶。
与阅读一起被时代抛弃的,还有一群嗜写如命的人和一个辉煌一时的职业。
被这个时代抛弃的,又何止这一群人,这一个职业。
一切就像梦一样。
一位位有能力有门路有跳板的同行纷纷辞职改行,一位位没能力存侥幸不甘心的同行寝食难安。
我是那些没有能力又缺乏安全感的一员。
我没有勇气辞职,也没有做他事的资本,我只有一支笔和一份情,我能做什么?
去年8月,我在保证自己正常工作的同时,加入自媒大军,业余时间开始做公众号。
眼看一年逼近,粉丝涨涨掉掉,订阅者不过万余人。而那些令人眼羡的自媒同行,早已站稳山头,拥有上千万、上百万或者几十万的粉丝。
多少个不眠之夜,码字完毕,浑身酸疼,两眼发黑,头晕脑胀,我都问自己:要不要坚持下去。
是的,我需要坦白的是,我没有想象的那么坚强,也没有写出的那么勇敢。
但我觉得,在阅读和书写的路上,我正变得坚强而勇敢。
今天,我依旧在不停地阅读,不断地书写,不屈地活着。
前途未卜,明天未知,但我已不再恐惧。
我越来越深切地意识到,生命的意义,在于接纳当前的每种境遇,并在此过程中看见的明亮与幽暗。
生活的质感,在于活成渴望的模样,并在此过程中留下的温煦与柔软。
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有梦。
过去的岁月,你们一点点向我袒露他们的脆弱与不堪,并希冀我能给予他们强大而有力的回应。
今天这个日子,我终于有勇气向你们诉说我的过往与忧伤,并希望你们能接纳我这真实的脆弱与脆弱的真实。
我要写的就这么多。
你们都要好好的。

——结束,是另一种开始——
闲时花开(公众号ID:ln13783770968),实名刘娜,80后老女孩,混迹媒体圈十余载,发表文字量百万字,问鼎晚报界最高奖,拥有情感文三百篇,被读者誉为“新闻界的八卦女人,情感界的知心记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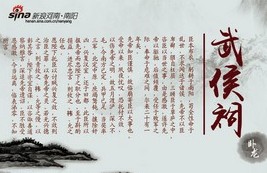





查看评论 0评论
发 表 登录|注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