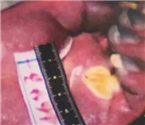我在矛盾纠结的心情中维持着表面婚姻。那样的日子只能算是“挨”。
挨了几年,我和史昱的情况并无改善,我们甚至已成了彻底的“最熟悉的陌生人” 。我们各过各的。这样的婚姻里,我出了轨——对方是我一个同事,那天是我25岁生日。原因很简单,情感与身体实在太寂寞,我像头困兽一样希望寻求一个出口。
我不知道史昱是怎么知道的,但他只是冷冷地说:“我理解你,一个年轻女人……”我给了他一个耳光,说:“我们离婚吧。”他却不同意,说他爱儿子,如果儿子跟着他,早晚也会变成同性恋。
我看着史煜,脑子里却冒出冯然的影子来。我不是想他,而是开始恨他了,因为我所有痛苦都是他造成的。如果不是他,我不会这么惨!命运这两个字,那时候已在戏弄我,我不知道自己将被命运带往何处。
转眼我就30岁了。这一年我决定离开小县城,出去闯一闯,要不我真要憋死了。我选择的是省城,也是我上大学的地方。
初来乍到的我跟个瞎子差不多,给人打过工,最终开了一间打字社,兼制作名片以及条幅啥的,生意还算可以。我的心渐渐平静下来。
D
故人已逝
时间不紧不慢地走到2002年,我35岁了。这一年我放弃了打字社,开起龙虾馆,生意兴隆得令人措手不及。很快我开了分店,接着我买了房、买了车,人生格局不知不觉中变大了。很自然的,我以一种胜利者的姿态重回同学圈。
只是我一直没离婚。儿子来省城读中学,住校,喜欢周末回来吃我做的饭。随着年龄的增长,史昱也似乎“正常”了许多,常跟我没话找话说,委婉地提出也想过来一起住,他可以开个小诊所啥的。我明白,说白了,就是想让我掏钱。彼时看史昱,我心里五味陈杂,这个帅气的男人如果能与我相爱该多好啊,可现实却是——他对我来说只是一幅画罢了。命运实在太会捉弄人。
2007年,蔷薇花爬满路边矮墙的时候,杳无音信多年的冯然突然出现在我面前——他直接加了我的QQ!看到验证栏里那几个字:阿秀,是我,冯然。我哆嗦得如同筛糠。这口气、这名字遥远得好像是上辈子的事了。他通过我的验证后,告诉我,他是从同学的博客辗转发现我的博客的,看了我的全部文章,他说:“我认定一定是你。阿秀,你好吗?”
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他的出现与消失一样都让人心碎。可是,他有什么权力这么欺负我?
他却说:“我知道你恨我,当年我没有主动站出来,我承认我是个缩头乌龟。我怕了,我逃了。后来跟父母提起,他们让我务必找到你。可等我问到你的同学时,才知你已经结婚了,孩子都有了。我深知自己怎么忏悔也弥补不了你,直到去年我才结婚,还没有孩子……”
我憋了近20年的一口气终于吐出来。我看着电脑屏幕,打不出一个字。
不久,他汇来一笔数目不小的钱款——之前他要我银行卡号,我毫不犹豫地给了他,我不需要钱,可我必须让他知道,他欠我的!还不了情,那就用钱还吧。汇款之后他却再没上过线,只留言给我:“我不想我爱人误会,往后请不要再联系了。”我当时气得差点砸了键盘,发出去几个字:姓冯的,你去死!
这是我最后悔的几个字——一年前,我意外得到消息,他已去世了,时间就是他给我留言后不久。原来他联系到我的时候就病入膏肓了。他没有留下后代。
我还能说什么呢?多少话埋在心里还没来得及说,他就不辞而别!那天我哭了个稀里哗啦,不仅为他,更为自己,真不知道是他害了我,还是我害了他!
斯人已逝,岁月不停留。转眼我也大半辈子过去了。现在的我看上去似乎是个幸福女人,有事业,儿子优秀,还出国深造了,老公在省城开着诊所,我似乎啥都不缺。说到史昱,我们关系还算融洽,他偶尔也会主动跟我亲昵。只是每当那样的夜晚,我都会梦回那个初夏,与冯然的那个初夏。
从22岁到49岁,有故事的年纪,我把自己都给了他,给了回忆,也给了恨。如今一切都成为过去,我不愿再记恨任何人。我只想努力珍惜身边人,并让自己好好的,这对于过去的那段情,也许算是一种和解吧。
(平顶山晚报)